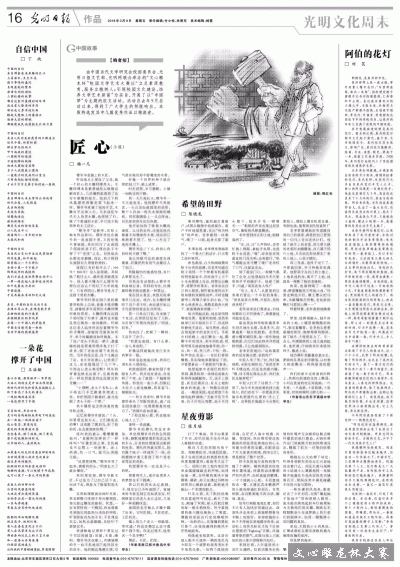编者按: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光明日报社文艺部、光明网联合主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承办的“文心雕龙杯”校园文学艺术大赛以“立足素质教育,服务立德树人;引领校园文化建设,培养文学艺术新苗”为宗旨,开展了以“中国梦”为主题的征文活动。活动自去年9月启动以来,得到了广大学生的积极响应。本版特选发其中几篇优秀作品以飨读者。
匠 心
浙江省绍兴鲁迅中学高三 杨一凡
穆爷爷是镇上的木匠。
听说他从小便没了父母,被一个好心的木雕师傅养大。木雕师傅本是紫禁城里头修缮宫殿的匠人,几经辗转流落到了这穷乡僻壤的地方。他刻刀下的凤凰漂亮得像是要飞起来一样。穆爷爷承袭了他的手艺,木雕水平出神入化。无奈战乱年代无人欣赏木雕,他便转了行,做了个普通的木匠,平日里干些简单的木工活计。
“穆爷爷”这称呼,实际上唯有我这样叫。穆爷爷住在镇外的一座废园子里,又因性情不喜喧闹,多次训斥了去废园子探险的孩子们,便在孩子中得了个“老怪”之名。而我每次去都安安静静,因此,我才得到在废园长久停留的特权。
废园已有好些年头了,100年?200年?没人说得清。其间换了数任主人,最终荒芜破落至今。别人都不懂为什么穆爷爷要住在这么个坍圮了大半的地方。只有我明白,穆爷爷是为了这园子里的木雕。
穆爷爷时常在园子里抚摸着那些染上尘埃、疲惫不堪的雕花,就像很多年前那位木雕师傅所做的那样。木雕师傅在这园子里叹惋了半辈子,最终也未能见到它焕然一新的模样。听闻这位老人临终时还拉着穆爷爷的手嘱咐,游廊的花窗该如何开,亭子的匾额该如何修复。末了说:“老头子我这一辈子,最遗憾的就是看着那帮洋鬼子打了进来,毁了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当年我没出息,自个儿跑出了京。老天爷发善心,让我到了这儿,安安稳稳活了几十年。可我这心里头难受啊!那年我背着包袱走出屋子,见着的最后一样东西就是我还没做完的花雕……”
“小穆啊,老头子有私心,舍不得这门手艺跟着我埋进土里。你把那园子修修好,就当是圆了老头子的一个梦。”
我不懂那是怎样深重的愧怍和念想。
记忆里穆爷爷曾说:“丫头,你看看这些木头。它们都是活的啊!这些断了翼的鸟,折了枝的花,也会感到疼的啊。”
彼时我抬着头,懵懵懂懂地问:“是像阿苗摔伤了一样疼吗?”好像世间之事,至伤痛也不过臂上一块瘀青。涂上药酒,吹一口气,就可以消隐无踪。
“还要更疼啊。”穆爷爷笑了起来,摸着我的头,“阿苗长大了就会懂的。”
我时常觉得,穆爷爷做木匠,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活下去,而活下去,则是为了修复那些木雕。
在那些缓缓流动的时光里,我也曾整日徘徊于亭台楼阁间,指尖掠过雕花的窗棂。我想,一定有那样的一个瞬间,我也曾感受到指尖的温热与浅浅的呼吸,听到那些花鸟的不甘,不甘湮没灰尘,如秋虫敛鞘翅,在枯叶下瑟瑟忍冬。
我清晰地记得那个看见过千百回的画面:旧屋,木凳,暖阳。穆爷爷伏在案上,布满皱褶的手一丝不乱地刻下起死回生的诏令。他的脚边堆满木屑,空气里有陈旧却不曾霉变的木香。
好像一个世界的种子就在那把刻刀下,破土成芽。
时光荏苒,岁月静默。小镇一如既往的宁静。
我一天天地长大,穆爷爷一天天地变老。他的腰杆不再挺直,一头白发如废园里的荒草,整个人犹如一枚失水皱缩的橘核。那双眼睛染上一点点浑浊,目光却依然专注而执着。
他开始加快了修复木雕的速度。以往我去时,还能见他在做着不知哪家的木凳,现在却已渐渐看不到了。他一心扑在了他的木雕上。
穆爷爷说:“丫头,我担心我的时间不够了啊。”
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消瘦着,好像把所有的气血都注入了刻刀。
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有什么事要发生了。
但我没有试图阻止穆爷爷的废寝忘食。那样的专注,仿佛最轻微的扰动都是一种罪过。
现在回头看去,我想有些事情早已注定。或许,在木雕师傅收下这个弟子时,命运就开始以无可逆转的姿态走向终局。
那一日我出门前,母亲接了个电话,在那里怔怔站了几秒,尔后放下听筒向我招手:“阿苗,回来。”
我站住了,犹疑了一瞬间,又迈开了步子。
“我要去废园。有什么事,一会儿再说吧。”
好像这样就能改变已发生的事实一般。
母亲急急地追出来,我却已消失在小巷深处。
我到废园时,静寂的园子里隐有人声。我并没有进去,而是转了个弯,去了废园一个偏僻的角落。那里有一座小亭,四根红木柱子上游龙蜿蜒,昂首奋飞,栩栩如生。
——昨日我来时,穆爷爷指着那条失了双眼的游龙,道:“这是园里最后一处需要修复的地方了。”语调兴奋如孩童。
“了却这桩心愿,我也能安心地入土了。”
谁料一语成谶。
穆爷爷的葬礼我没有参加。我觉得穆爷爷仍然在那园子里,静默地摩挲着那些活过来的木头,古老的纹理斑驳出崭新的色彩。葬礼时我就在那儿,独自像个疯子一样地哭了一场,泪眼蒙眬中重又看到了那个苍老却笃定的身影。
我想穆爷爷一定还是开心的吧。
看着两代人,或许是更多人的梦想在手下圆满。
那以后我再未去过废园。不,现在它已不叫废园了。省城来的专家见到它后如获至宝,听闻修复它的老人业已过世,又是好一阵扼腕叹息。
废园的名字被从古籍中翻了出来。它叫匠园。木匠的匠,工匠的匠。
镇上的几个老人一拍脑袋,笑叹道:“我说老穆怎么总守着那个园子呢。你还记得不,他单名一个匠字啊!”
穆匠。木匠。匠园。
指导教师:李 莉
《光明日报》( 2018年03月09日 16版)
希望的田野
陈晓龙(山东省东平高级中学高三)
寒风嘶吼,猛烈敲打着窗户,试图从缝隙中钻进屋内。窗户不时地摇晃着,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老李感到一丝寒气,嘬了一口烟,起身关紧了窗户。
冬季农闲,老李便来到城里找了一个看大门的活计,打点零工添补家用。
夜色渐深,白天热闹喧嚣的院子出奇的寂静,但老李知道在院子里那一个个种着有机蔬菜的明亮温室中,却有成千上万个小生命要破土而出,将要长出嫩芽,将要孕育果实。老李坐在自己的小屋里,倾听着电视传出不绝如缕的戏剧唱词声,不时也随着哼上两嗓子家乡的小曲,“鸟奔山林虎奔山,喜鹊老鸹奔大树下,家雀哺鸽奔房檐……”
每当唱起这曲,他总是唱得喉咙发烫。他喜欢热闹,虽然来城里已有不短的日子了,但这样的静他不适应。每当黑夜,他总会想起家中的老伙计们。冬夜乡村的晚上,他们聚在一起,聊聊今年的雨水,来年的收成,吧嗒吧嗒乐滋滋地抽着旱烟,你一言,我一语,笑几声,干咳一阵,咳声传出老远……老汉们看似懒散,其实暗地里都铆足了劲,开春要拿出一个崭新的气象来。
他想起家中老屋后的那片菜园,蔬菜的那一抹绿总是被太阳照得油腻腻的。天,说不上很蓝,甚至泛着灰白,有点土地和粮食的味道,有一种踏实的舒适。一踏进菜园,他总要放下水桶吼起野调调:“芝麻开花节节高,谷子开花压弯腰,茄子开花头朝下,苞米开花一嘟噜毛……”粗哑的声音击荡过层层空气,像股热风肆意飘扬。
老李想到村庄和土地,眼睛湿润了。
“汪、汪、汪”几声狗吠,老李忙披上棉服,拿起手电筒,走进院子去巡查。“噫”,原来是有间温室的门没关呐,还亮着灯。“热气都跑出来可糟了喽!”老李叹了口气,往温室走去。
到了温室门口,一股暖气裹住了全身,让他想起往年冬天家里热乎乎的碳炉子。他搓了搓手,问道:“里面还有人吗?”
“有人,有人”,从葱茏的豆角架后冒出一个年轻的身影,“原来是李大爷啊,外面冷,您快进来吧!”
老李原本没打算进去,但他的脚却已不听使唤了,挟裹着他向温室走去。
温室里各种作物和蔬菜争先恐后地生长着,虽是冬天,却像盛夏一般生机勃勃。老李张着大嘴环顾四周,每一样作物他都熟悉,但它们如此秩序井然地排列着,又让他感到陌生。
老李好奇地问:“这些蔬菜真的没有施化肥、农药吗?”
年轻人笑了笑:“对,我们施绿肥,采取生物防治。”虽然老李听不懂这些,但还是很感兴趣:“哦,怪不得长得这么好,我们农民也能种吧?”
年轻人打开了话匣子:“当然了,如今中央的政策扶持力度很大,我们农村下一步要逐步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的‘沃土工程’。这种技术能减少不合理化肥投入,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利润也高,能帮助农民致富呢!”
老李带着满脸的笑意踱回到自己的屋里,真想把自己看到的一切马上告诉老伙计们。他搓了搓手上的老茧,那又厚又硬的老茧时刻提醒他,自己属于那片土地,只有站在那块厚实广袤的土地上,心里才踏实。
再三考虑,他终于定下了,开春就回家,学习种植有机蔬菜。他要坚守在自己的土地上,土地是他的命,离开了土地,他就是一棵断了根的老榆树。
夜里,他破例喝了一壶烧酒,醉意朦胧里又哼起小曲,“你要走啊他不拦,霸王槽头把马牵,先解缰绳后背鞍,老仙家扬鞭打马要回山啊……”
哼着哼着,老李甜甜地睡着了。
梦里,他挥着锄头,刨开冰冻的土地,土壤冒着腾腾的热气,散发着馨香。老李抬头看看温暖的阳光,脱掉厚厚的棉袄,搓了搓手,干得更卖力了。不一会儿,布满裂痕的土地又温润起来,他笑着,仔细将来年希望的种子,撒进土里。
他仿佛听到藤蔓恣意生长,肥硕的瓜果在拍手歌唱,从村委大院里飘来一阵阵甜美的歌声——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冬麦,一片高粱,十里荷塘,十里果香,哎咳哟嗬呀儿咿儿哟……
(指导教师:吴绪磊)
《光明日报》( 2018年03月09日 16版)
星夜剪影
张月瑶(北京市第五中学高三)
打了个寒战。我不由裹紧了外衣,却仍旧抵不住冷风钻入裤腿的凉意。
晚自习后的双眼有些干涩。我略微抬首,快速眨眨眼,星子在夜空映出的熟悉的光影再度提醒着我:离高考又近了一天。胡同口的工地内依旧传来金属碰撞敲击的声响,如同沧海一粟,在呼啸的寒风中被稀释、碾碎,却又在拂过耳畔的刹那同心跳跃动着,渐渐地共振出一个和谐的鼓点。
行至主街,失了阻挡的寒风恣意地呼号而过,麻木了指尖,割痛了双颊,侵入四肢百骸的每一根末梢神经。怀中紧抱着的练习题也被染上了寒意,薄脆的纸张在行走间噼啪作响,一如我的心,在斑斓的霓虹灯影下,在张扬凛冽的晚风中茫然地摇曳。
我倏地有些想笑。这沓在他人眼中只是废物的纸页而今却在一个逐梦的高考考生手中曳然生姿,一如两个孤独的灵魂,在茫茫人海中相遇、纠缠。恍惚间,我仿佛觉得这些脆弱的纸张便是萦绕在我心头的最为珍贵的宝藏,在眼前这个灯火迷离的夜晚,拥有它们,便是拥有了整个世界。
猝不及防地与食物的香气撞了个满怀。暖烘烘甜丝丝的烤红薯味道,伴着街边冰糖葫芦的叫卖声,如同流溢的糖稀,一寸寸地淌入心底。不经意地投去一瞥,正遇见卖冰糖葫芦的人被冻得通红的面孔。含笑相视,各自默契地不再言语,擦肩、离去。
信号灯刺眼地亮红着,却仍不乏有人加快步伐溜过去。迎面快步走来的上班族频频看向手腕上的指针。身旁夜跑的小伙子不停地在原地踏步热身,运动衫上的荧光标在月色下反射出惹眼的“Fighting”字眼,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在斑马线上川流如织的人影中显得格外灿烂。
来到对街,人行道旁的小店灯火通明。拉面店服务生热情的吆喝声交杂着街边鞋店循环播放的流行歌曲,火锅的蒸汽在门帘被掀开的刹那喷涌而出,朦胧了前方一对情侣依偎的身形。
刚刚在公交站牌下站定,听得身旁候车的母女正兴奋地谈论着什么。却见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小心翼翼地将一张被整齐地叠在书包夹层的奖状铺展而开,梨涡浅笑中满是掩藏不住的兴奋与期待。
一阵冷硬的风刮来,眼底泛出了少许泪花,对街“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标语映入眼帘。流水般次第亮起的车灯被晕染为无数绚烂的光圈,倒映在无数默默奋斗在逐梦路上的行者们的眼眸中,如同一颗颗渺小却闪耀的星辰。
星辰,无数枚小小的星辰,汇聚成悬挂在都市夜晚的最为璀璨浩瀚的星河。
那是梦的海洋。
(指导教师:朱香平)
《光明日报》( 2018年03月09日 16版)